
辽思河畔,与一座书院的光阴对话
暮色未沉时抵达大朱家村,辽思河的水正绕着船形盆地缓缓流淌,像一根银带,轻轻系住了岸边的紫阳书院。远远望去,灰瓦在树影间若隐若现,风火墙的曲线划破天际,倒像是给这方水土,圈住了一块沉淀着墨香的秘境。

踏过青石板的刹那,脚步不由自主放轻了。正门门额嵌着一方石匾,行草"紫阳书院"四字笔力遒劲,墨色虽经风雨浸蚀,却仍透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,仿佛是哪位文人挥毫而就,让这扇门从此成了连接尘世与文脉的渡口。两块石碑立在书院外,风雨侵蚀让字迹有些斑驳,却愈发显得郑重——就像两位守了八十年的老者,把1940年建院的故事,藏在每一道裂痕里。伸手抚过碑面,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冰凉的石质,更像是触到了一个时代的体温:那时的匠人如何垒起砖木,那时的学子如何踏过门槛,都在这沉默的刻痕里,悄悄呼吸。

推开虚掩的木门,吱呀一声,仿佛撞开了时光的暗门。前厅正中,汉白玉朱熹雕像静静伫立,衣袂翩然如沐春风,目光穿越八十年光阴,仍带着劝学的温厚。转身看身后木板墙,《朱子家训》的字句整齐排列,"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"的箴言,在光影里泛着淡淡的木纹,让人忽然想起:这座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建的书院,曾在五十年代化作朱氏祠堂,文脉与族亲的根系,竟在此处交织成更密的网。

硬山式屋顶下,三进院落层层递进,天井里的光斜斜落下来,在青石板上投下窗棂的影子。前楼与中厅之间的木梯还留着磨圆的棱角,想来是无数双布鞋踏过,才把坚硬的木头磨出了温润的弧度。二楼走廊的栏杆雕着简单的花纹,扶上去时,恍惚能听见细碎的脚步声——许是当年的学子捧着书卷,正从这里走过,衣袂扫过栏杆,带起一阵淡淡的墨香。

最让人驻足的是后厅。"孝思堂"的匾额悬在正中,金字在昏暗中仍透着庄严,八角井平箅的天花将光线筛成细碎的网,落在神龛前的石台上。这处带着中西合璧痕迹的建筑,竟把肃穆与灵动融得恰到好处:木梁的古朴、砖石的厚重,与天花的精巧纹路相映,像在诉说着建院时的用心——既要承续文脉,又要容纳新思。指尖划过斑驳的木柱,木纹里还嵌着些许墨渍,不知是哪位学子临帖时不慎滴落,竟让八十年后的访客,仍能嗅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松烟香。

后花园的草色漫到石阶边,几株不知名的树正落着细碎的花。站在这里望出去,辽思河的波光与远处的青山叠在一起,忽然懂了为何书院要择址于此。读书人的襟怀,原是要借这般山水来养的:看河水汤汤,便知逝者如斯;望青山巍巍,方悟学无止境。想来当年的学子们,课罢会在此徘徊,让书页间的道理,与眼前的草木晨昏相融,才把知识真正酿成了心底的底气。

暮色渐浓时,管理员说要锁门了。转身离开的瞬间,夕阳正为"紫阳书院"的石匾镀上金边,字迹忽然清晰起来,像是被重新点亮。回望书院,它静静地伏在盆地里,灰瓦与树影交织,倒不像一座建筑,更像一位沉默的智者——不喧哗,不张扬,却把八十年的风雨、八十年的文脉,都酿成了辽思河般的绵长。

归途上,河风带着水汽拂过脸颊。忽然明白,紫阳书院哪里是在等待寻访者,它早已把自己化作了这方水土的一部分:河水流过,是它在低语;青山矗立,是它在守望;墙上《家训》的字句与雕像的目光相和,便是它在时光里,写下的新的篇章。而我们这些偶然到访的人,不过是借它的门扉,短暂地住进了一段温润的光阴里,带走满身的墨香与山水气,好让那份对知识的敬畏,在寻常日子里,也能悄悄生长。
(白春明 2025.8.5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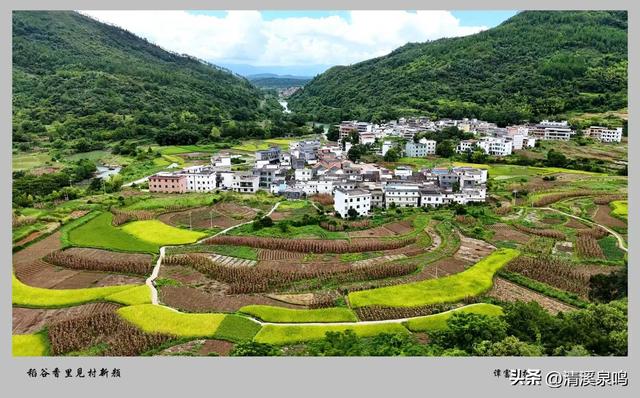
(部分图片来自文友致谢)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