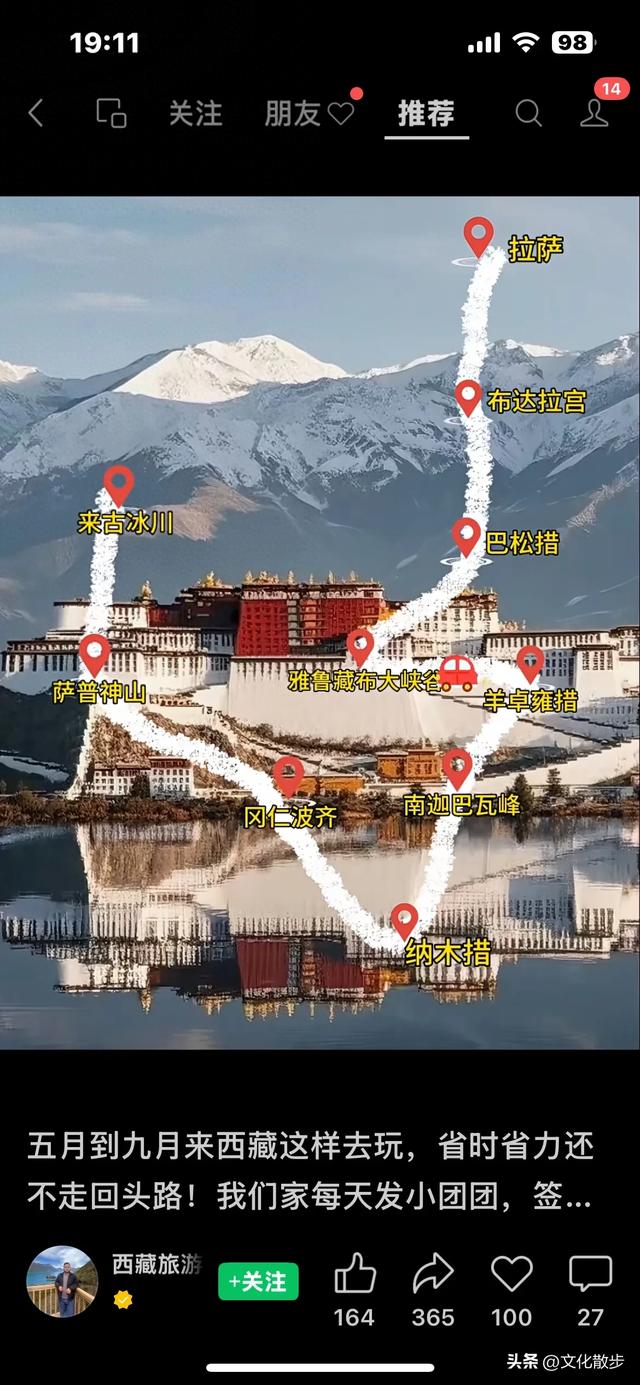
18日傍晚6时33分,我们怀着对世界屋脊—青藏高原的向往,正式踏上了奔赴西藏的旅程。
从上海站出发,搭乘Z164次列车一路向西南行进;
19日晚上7点半,列车准时抵达西宁站,我们在此换乘专门配备有氧设备的车厢——这是为适应后续高原低氧环境所做的关键准备,也是青藏铁路客运服务中极具人性化的设计。
接下来的行程,列车将驶入被誉为“天路”的青藏铁路段,而这段路程也让我们对这条奇迹之路的敬意愈发浓厚。
要知道,青藏铁路的建设难度堪称世界铁路史上的巅峰挑战:
它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达960公里,翻越唐古拉山时最高海拔更是突破5072米,是全球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;
沿途不仅要面对永冻土层的“难题”——冻土层夏季消融会导致路基变形,建设者们便创新采用“主动降温”技术,通过铺设通风管、保温板等,让路基在严寒中保持稳定;
还要跨越可可西里、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,为了保护藏羚羊等珍稀动物迁徙,专门修建了25处野生动物通道,让铁路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随着列车渐渐靠近拉萨,窗外的风景换了模样。灰蒙蒙的天空,辽阔的草原上缀着零星的牦牛,远处开始出现顶覆金瓦的藏式民居,我的心像被风吹起的经幡,雀跃得停不下来。
可就在这时,身旁的爱人突然轻声说头晕,还伴着轻微的恶心——是高原反应来了。
我赶紧找列车员求助。恰好,列车员巡查时正在车厢,看到这一幕,立刻过来帮忙用上列车配备的应急吸氧装置,还耐心叮嘱我们:“快到拉萨了海拔还在升,别着急活动,尽量少说话保存体力,到了酒店先歇着别洗头洗澡。”
40余小时的长途跋涉后,20日18时左右列车终于缓缓驶入拉萨站。
我们走出车站,乘坐旅游公司提供的车辆,到了提前预订的住处。
原以为休息一会儿会好转,可爱人躺下后,头痛、恶心的感觉不仅没退,还添了些心慌。
询问酒店前台人员,她告诉我们:“出门左拐就有诊所,专门看高原反应的,很多游客都去那儿看过,放心。”
我们扶着爱人往诊所走,推门进去时,里面已有几位同样因高反来就诊的游客。
医生简单询问症状、测了血氧和血压后,说:“是典型的急性高反,先输点液补充电解质,再吸会儿氧,很快就能缓解。”大概一个小时后,爱人终于说“头不晕了,也不恶心了”,脸色也比之前红润了些。
回酒店的路上,爱人感叹道:“幸好有这诊所,不然这趟西藏行刚开始就要‘垮’了。”
此刻我才真正觉得,这场旅程不仅有对“天路”奇迹的震撼:
那些用智慧和热血攻克难关的建设者,让雪域不再遥远;
更有直面高反时的揪心与万幸——陌生列车员的援手、诊所的及时救治,还有同行朋友彼此的相互照料。
这些细碎的温暖,让这段初遇高原的经历,多了份难忘的温度。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