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漫步沙隆达广场,总会想起小时候跟着爷爷来这儿。那时候广场还叫便河广场,没有现在这么整齐的地砖,靠近北京路的地方有个小市场,卖棉花糖的推着车穿梭,爷爷总买一支粉色的给我。我举着棉花糖在人群里跑,看见有人在河边放风筝,风筝线能拉得老远,线轴转得“嗡嗡”响。现在河边早就填成了平地,可一走到广场南边,总觉得还能听见当年的风声。

这片地方的故事,得从“便河”这两个字说起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沙市的工厂特别景气,电冰箱、洗衣机卖到全国各地,连武汉人都专门坐车来买。那时候的便河广场周围,光是卖小商品的摊子就排了半条街,有修钢笔的、配钥匙的,还有摆摊算命的。傍晚时分最热闹,下班的工人、放学的学生、买菜的主妇挤在一块儿,路灯一亮,各个摊子的灯泡像星星似的。老人们说,那时候的沙市叫“小上海”,便河广场就是“小上海”的客厅,谁家里来了亲戚,都要带到这儿转一圈。
1999年广场重建,名字改成了“沙隆达”。那会儿沙隆达集团正红火,是荆州的大企业,出钱帮着建广场,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。新广场比以前大了不少,添了电视墙,还有九级跌落式的水池,喷泉一开,能引得好多人来看。但最让人记得住的,是刚建好时放的四尊维纳斯雕像。汉白玉做的,有两米高,结果才摆了四天,就因为有人说“不好看”被拆了,现在只留下四个贴了瓷砖的墩子,成了老沙市人聊天时的笑谈。

广场的功能变了好几次,可总离不了荆州人的日子。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到这儿,那天广场挤得满满当当,所有人都举着小国旗,火炬手跑过的时候,欢呼声能盖过旁边马路上的汽车喇叭。平时没这么热闹,却更有人情味。早上是老人的天下,跳广场舞的、甩鞭子的、练嗓子的,各占一块地方;中午太阳大,就成了外卖小哥的歇脚点,几个人围着电动车坐在花坛边,打开饭盒聊两句;傍晚最热闹,广场舞队能分好几拨,中间隔着几步路,音乐却互不耽误;年轻人不爱凑这个热闹,多在休闲广场那边散步,或者坐在台阶上看手机,偶尔有卖冰粉的推着车经过,吆喝一声,总能围上几个身影。
广场上的那些东西,慢慢都成了荆州人的记号。超高的路灯杆,顶端像一个飞碟;大花钟的指针走得慢,报时的古筝声总比广播里的时间晚半分钟,可每天到点了,还是有人抬头看;九级跌落式水池的第三层总爱漏水,修了好几次也没彻底好,孩子们却专爱往那儿跑,说“漏下来的水溅在脚上凉快”。
这两年总有人说,沙隆达集团都改名了,广场是不是该改回“便河广场”。有人觉得该改,说“便河”俩字有故事,卞和献宝的传说听着就有文化;也有人觉得不用改,说“沙隆达广场”叫了二十多年,早就听顺了口,改了反而不习惯。其实争来争去,争的不是名字,是想留住点啥。老人们怕年轻人忘了便河的样子,年轻人怕老人们总活在过去,可不管怎么争,每天早上的广场舞还在跳,傍晚的孩子们还在水池边跑,这广场就还是那个装着所有人日子的地方。
听说管理部门打算给广场添点新东西,要装几个直饮水机,再在角落里加些充电插座,还想在休闲广场那边弄个小舞台,让民间的戏班子能来唱唱戏。有人担心加了这些会变味,其实不用怕。就像当年从便河变成广场,从旧名字变成新名字,只要来这儿的人还在,故事就还在续写。路灯杆不会因为多了直饮水机就失去味道,花钟也不会因为有了充电插座就停摆,就像荆州人过日子,总在老习惯里添点新意思,日子才过得有盼头。

沙隆达广场就像块拼了几十年的拼图,便河的热闹是一块,重建的新鲜是一块,奥运火炬的欢呼是一块,广场舞的音乐是一块,连那四个空墩子都是一块。缺了哪一块都不完整,拼在一起,就是荆州人这些年的日子。
你呢?你跟沙隆达广场有啥故事?是小时候在这儿丢过一块橡皮,还是跟对象在花钟旁表过白?你希望广场以后添点啥?欢迎在下面说说,让咱们的这块拼图,再多几块新花样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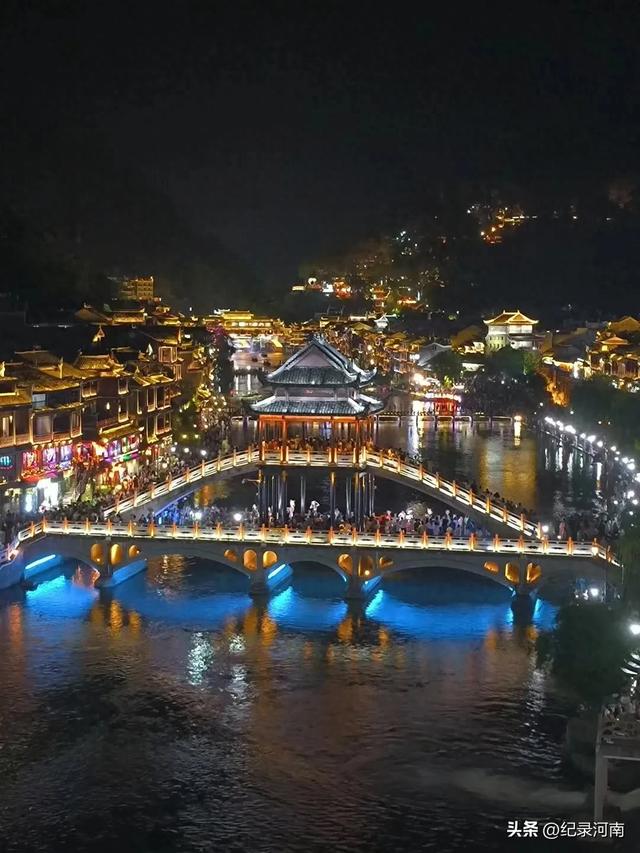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