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新郑机场起飞那会儿,河南的秋老虎正凶着,日头晒得柏油路冒烟,空气吸到肺里都发烫。落地沈阳桃仙机场,机舱门一开,嗬!一股风兜头盖脸就撞上来——不是咱家那种闷热风,是干爽利索、带着点凉气的风,像三伏天猛地灌了一口井拔凉水,从嗓子眼儿一直舒坦到肚脐眼儿。一块儿来的河南姐们儿一把掐住我胳膊:“老天爷!这风是活的!比黄河滩上的野风还透亮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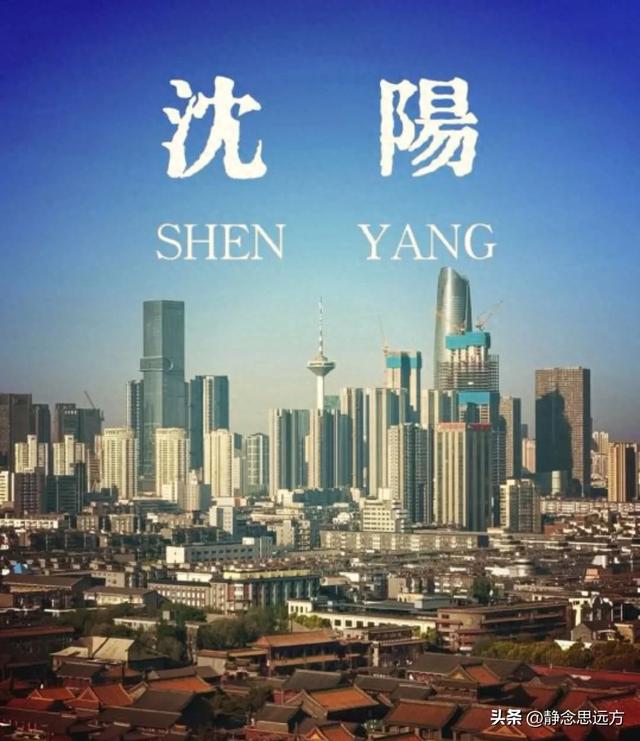
大清早五点钟的中山路,地砖还湿漉漉的。扫街的大爷拖着大扫帚,“唰——唰——”声在空旷的街上响着,惊得砖缝里找食儿的麻雀扑棱棱飞起。那些老方砖,年头久了,被踩得油光水滑,天蒙蒙亮的时候,砖面上的小水坑里,映着两边老楼房的尖顶、圆顶的影子,晃晃悠悠,像把半条街都泡在了一个大水盆里。

最得劲儿是后半晌。日头一斜,把楼影子拉得老长老长。砖缝里存的雨水成了碎玻璃碴子,映着天上跑的云彩和房顶。卖老汽水的小摊点起了灯泡,昏黄的光从绿玻璃瓶子里透出来,在地上晃出一片一片的光晕。一个戴着前进帽的老爷子,坐在马路牙子边的马扎上,手里盘着俩油亮的核桃,瞅着来来往往的人乐:“你们河南的龙门石窟,那是‘立’着的,石头刻得老高;咱沈阳这地界儿,是‘蹲’着的,老楼老厂子跟人一块儿喘气儿过日子。”正说着,风卷着片发黄的杨树叶打着旋儿飘到他脚边,叶子上沾的那点亮光,像从旁边老建筑墙皮上蹭下来的金粉。

专门挑了个阴天去沈阳故宫。刚走到宫墙根儿底下,雨点子就砸下来了,细细密密的,跟天上有人往下撒小米儿似的。雨水顺着大青砖的墙缝往下淌,顺着琉璃瓦的檐儿往下滴,“吧嗒吧嗒”落在青石板上,溅起的小水花里,模模糊糊能瞅见红墙金顶的影子在里头晃。

几只灰鸽子躲在殿檐子底下,抖搂着翅膀上的水珠儿。一个穿红塑料雨衣的小丫头,手里捏着半拉馒头,蹲在滴水檐下等鸽子过来。鸽子歪着脑袋瞅她,尾巴尖儿上的水珠掉在她胶鞋上,吓得她一缩脖子,“咯咯”笑起来。雨水把大殿的木头格子窗洗得发亮,日头偶尔从云彩缝里钻出来,红的、绿的光斑就跳在那些雕花的门窗上,晃得人眼晕,连那殿门上的铜钉都像活了似的。
头一回站浑河边儿上,心里头一下子觉得黄河水太“躁”了。这浑河的水面是铺开的,望不到头,水色发青,像一大匹被揉搓过的厚棉布。浪头也不急,“哗——哗——”,慢悠悠地舔着岸边的石头,退回去的时候,留下一片湿漉漉的印子,映着天上压得低低的云。
等日头完全掉进浑河那头,天“嗖”一下就凉了。河对岸的灯,一盏接一盏亮起来,在河面上碎成一片星星点点。有个穿夹克的小年轻抱着吉他坐在河堤台阶上,哼哼唧唧唱着《沈阳啊沈阳》,调儿都跑到姥姥家了,风把歌声扯得断断续续,可听着心里头反倒踏实。我裹紧了带来的薄外套,忽然就明白沈阳人那股子“敞亮”劲儿打哪来了——黄河边的堤坝是高的,水是急的;浑河的岸是敞开的,风里头混着水汽、草腥味儿,还有远处工厂隐约的汽笛声,能把心里头那点拧巴疙瘩都给吹平展了。
从中山路拐进铁西那些老厂区,像一脚踩进了过去的年月。苏联援建那些大厂房的墙皮,大片大片地往下掉,露出里头红褐色的老砖头。砖缝里钻出些叫不上名的野草,在风里头摇啊摇。有的厂院墙上,还模糊留着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的大红字,旁边可能就是一根粗大的、锈迹斑斑的蒸汽管道,像个倔强的老工人。
最打眼的是那些窗户。有的窗户框还是老式的木头格子,糊着发黄的报纸,却贴着崭新的“福”字窗花;有的窗台上摆着掉了漆的铁皮饼干盒子,里头种着几棵蔫头耷脑的绿萝;有扇老楼的窗户玻璃上,还留着冬天冻出来的冰花印子,弯弯绕绕的,像谁用手指头在冰上画的画儿。下午的日头斜斜地照进来,把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,印在斑驳的墙上,像给这老房子盖了个戳儿。一个扎俩小辫儿的闺女趴在窗台上写作业,铅笔头在纸上“沙沙”响,混着墙根儿蛐蛐儿的叫声,一下子让人想起老家村头写作业的光景,可又多了股子东北的硬朗劲儿。
走那天,飞机从浑河上头飞过,我瞅着底下那条灰亮灰亮的河带子,猛地想起河边那老爷子的话:“沈阳的魂儿,不在冬天的雪壳子多厚,在秋天的风里——风里有河水的软乎劲儿,有老厂房的硬实劲儿,还有过日子的热乎气儿。”
可不咋地!这城不光是“老工业基地”一个名号能框住的。它的好,是中山路老砖上反的光,是沈阳故宫雨里湿漉漉的鸽子叫,是浑河慢悠悠的水溜子,是老厂区墙缝里钻出来的那抹绿。它像一碗刚出锅还烫嘴的老四季抻面,头一口下去是咸香,嚼着嚼着麦子味儿就出来了,让你回家了咂摸咂摸嘴,还惦记着那股子实在劲儿。
下回开春儿,高低得再来看看它开化的模样——估摸着那时候,柳树条子一抽芽,比九月的浑河水,更有活气儿。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