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雁塔:千年古塔的时空对话
——三秦大地见闻之七
作者:黄企生
晨光中的大雁塔,像一枚青灰色的印章,在西安的天际线上盖下深沉的印记。

穿过北广场涌动的人潮,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正随着《梦回大唐》的旋律起舞,水柱腾空时折射出的彩虹,与远处古塔的剪影奇妙重叠。
这或许就是西安最动人的姿态:
让盛唐的月光与现代的霓虹共舞。
踏入大慈恩寺的朱漆山门,喧嚣骤然被隔绝在红墙之外。

庭院里的古柏已有百年树龄,枝干如虬龙般伸向天空,树影婆娑间,七层塔身愈发显得庄严。
这座由玄奘法师亲自主持修建的佛塔,最初只为存放他从印度带回的657部佛经,如今却成了跨越千年的文化坐标。
仰头望去,青砖砌就的塔身虽历经风雨侵蚀,砖缝间的苔藓却透着倔强的生机,底层门楣上的线刻佛像仍清晰可辨,飞天的飘带仿佛还在微风中轻拂,那是初唐工匠用錾刀刻下的永恒。
拾级而入,塔内光线骤然变暗,一股混合着木质楼梯与陈年香火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
狭窄的旋梯仅容一人通过,扶手被历代访客摩挲得发亮。
一阶一阶向上攀爬,仿佛在穿越时光的隧道:
二层的铜质释迦牟尼佛像前,几位信徒正虔诚跪拜,烛火跳动的光影在斑驳的墙壁上摇晃,与明代修复时留下的彩绘残片相映成趣;
三层的大雁塔模型旁,导游正讲述着它的"成长史"——从最初的五层楼阁式砖塔,到武则天时期加盖至十层,再到历经兵火后定格为如今的七层,每一次改建都是一段历史的注脚。
最触动人心的是四层的陈列。

玻璃展柜里,一卷泛黄的《大般若经》复制品静静躺着,字迹娟秀如行云流水。
讲解员说,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十九年,每日笔耕不辍,共译出佛经75部、1335卷,而这座塔就是他最忠实的守护者。
墙角的展柜里,一枚佛舍利在射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,虽不及拳头大小,却似有千钧之力,让人想起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师徒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——原来神话的底色,从来都是凡人的执着。
攀至顶层时,风忽然大了起来,吹动着塔檐悬挂的铜铃,"叮咚"声清脆如盛唐的余响。

凭栏远眺,西安城的轮廓在阳光下铺展开来:
南边的曲江池波光粼粼,据说那里曾是长安仕女泛舟的场所;
北边的明城墙如绿色的绸带环绕城区,而更远处的高楼大厦正拔地而起,玻璃幕墙反射着天光。
玄奘当年译经时,是否也曾站在这里眺望?
那时的长安,朱雀大街上车马辚辚,西域的驼队载着香料与宝石穿行而过,与如今地铁呼啸而过的轨迹,在时空中完成了一场沉默的接力。

塔下的玄奘广场上,法师的铜像手持经卷,目光坚定地望向西方。
几位白发老者正围着棋盘对弈,棋子落在石桌上的脆响,竟与不远处孩子们诵读《心经》的童声奇妙地融合。
寺外的文创店里,年轻人大胆地将塔影印在T恤上,把佛经里的箴言刻成书签——原来传承从不是刻板的复制,而是让古老的智慧找到当代的表达。
暮色渐浓时,再次来到北广场。


音乐喷泉的表演已近尾声,最后一束水柱落下时,恰好有晚归的飞鸟掠过塔顶。
灯光次第亮起,给古塔的轮廓描上金边,也照亮了广场上匆匆而过的行人:
有背着行囊的旅人,有推着婴儿车的夫妇,有打太极的老人......
他们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,有着不同的故事,却都被这座塔默默注视着。
离开时回望,大雁塔的剪影已融入夜色,唯有顶层的灯笼还亮着,像一颗不肯沉睡的星辰。

忽然明白,它之所以能在岁月中屹立不倒,不仅因砖石的坚固,更因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对智慧的渴求、对信念的坚守。
就像玄奘法师当年西行的背影,既是向历史的致敬,也是对未来的奔赴——而这,或许就是所有伟大文明共同的密码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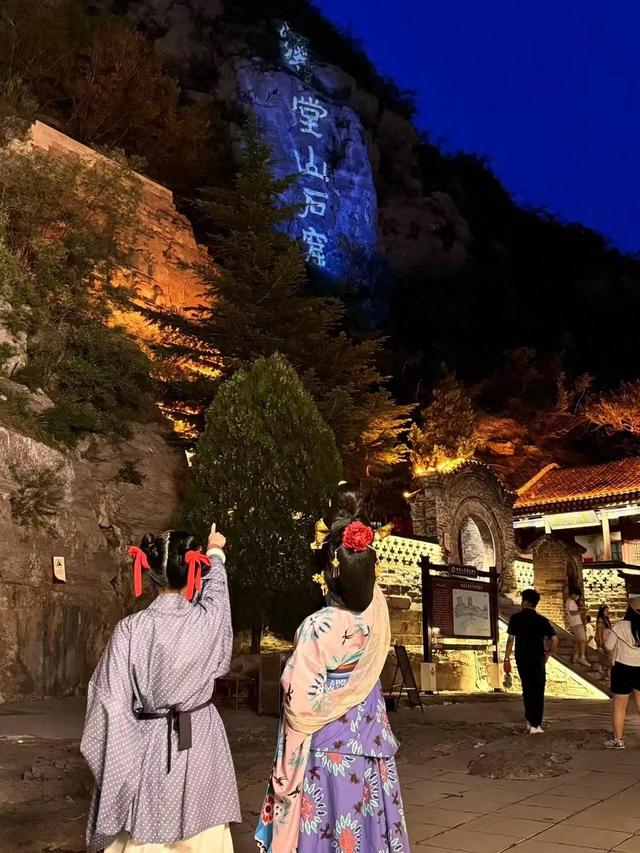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