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至那天,我第一次游明十三陵。确切地说,是第一次游览十三陵神道,亦即进入长陵前的前导和序曲,每每被人所忽略的一段。以前看旧京老照片时发现十三陵神道有种苍凉之美,故而很想看看今日同一景致沧桑几何。
天光尚早,我便站在了那座巨大的石牌坊之下。
五间六柱,顶天立地,白石在晨光里泛着清冷的光。这是主神道的起点,大明王朝通往幽冥世界的巍峨门庭。六百余年的风霜只在其上留下些微的、模糊的刻痕。这座建于嘉靖十九年的石牌坊,用青白石料雕琢而成,高14米,宽28.86米,是我国现存营造时间最早、建筑等级最高的大型仿木结构石牌坊。牌坊夹杆石四面雕刻着八对狮子滚绣球和十六条云龙图案,在晨光中仿佛流动着时光的倒影。我很想伸出手掌,轻轻触摸牌坊微凉的柱身和那些细腻精致的浮雕,可惜如今石坊已被一圈木栅栏团团围住做整体保护,人们只可远观而无法靠近。之前看到十三陵的老照片,石牌坊周边空旷无物,直接映出远处的天寿山,它像一个沉默的巨人,兀自矗立,无论人间如何喧嚣或沉寂,显出一副独孤求败的苍劲凄然。如今牌坊北面绿树成林,乃至将原本的神道悉数遮挡,也自然削弱了昔日那一份傲然的皇族气象。
沿今天的昌赤路向北行,约1.3公里处,大宫门便赫然耀目。这座陵墓区的正门,是陵区的总门户,俗称大红门,庄重而肃穆。它坐落在东西的龙山和虎山之间,中门正对天寿山主峰,气势非凡。大红门墙体为红色,单檐庑殿顶,上覆黄色琉璃瓦,下承石刻冰盘檐,辟三券门。过去,这里戒备森严,中门是已故皇帝、皇后棺椁和神主、神牌、祭品、仪仗通行之门;左门是当朝皇帝谒陵通行之门;右门是谒陵官员进入陵区所经之门。门口左右立下马碑二方,正面刻有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八字。在明代,奉旨官员到此,文官下轿,武官下马,皆步行进入陵区,否则以大不敬论罪。民国时期,这里逐渐沦落成荒草丛生的空旷之地,只有几名衣衫褴褛的守陵人偶尔从这里经过。他们佝偻着背,在夕阳下拖出长长的影子,与周围空旷的天地融为一体。那时的大红门斑驳的朱漆剥落殆尽,像被时间遗弃的废墟。如今,大红门经过修缮,朱红大门在阳光下焕发出庄重而温暖的光泽,门洞里已不再有往日的荒寂,而是绿荫成行。
穿过大红门,神道两侧的景致开始变得丰富起来。距大红门0.6公里处,长陵神功圣德碑亭矗立眼前。这座重檐歇山式建筑,正方形,四面辟门,高约三丈,建于宣德十年(1435年)。亭内是明成祖永乐帝朱棣的神功圣德碑,碑阳刻的是明仁宗朱高炽为其父朱棣撰写的三千余字颂赞碑文。碑阴刻的是乾隆五十年(1785年),清高宗撰写的《哀明陵三十韵》,具体从明十三陵建立的过程中,乾隆如何称赞永乐皇帝,并且历数了明朝皇帝的丰功伟绩,同时指出了他们的弱点和败笔之处,分析明朝是如何丢了江山,以此告诫后来的继承者。碑亭四隅各立一座高10.81米的汉白玉华表,每座华表上共刻有四十一条龙。近代以后,这些华表四围长满了齐人高的荒草,碑亭的屋顶破败不堪,几根梁柱歪斜着,仿佛随时会坍塌。而此刻,阳光透过神道两侧新栽种的柳树的枝条,在石碑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碑亭的飞檐翘角上,几只麻雀在跳跃啁啾,与碑亭内游客的轻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。
沿着神道继续前行,800米的距离里,石像生依次呈现开来。这些石像生同样建于宣德十年,以一对石望柱起首,其后排列有石兽12对,石人6对。石兽每种两对,狮子、獬豸、骆驼、象、麒麟、马各四匹,两卧两立分列神道左右。石狮威猛雄壮,凛然不可侵扰;獬豸是传说中象征公允正义的神兽,被认为能辨曲直,有触不直者;骆驼为沙漠之舟,象征运输;大象聪慧温厚,象征祥瑞;麒麟是传说中的神兽,古人认为如有麒麟出现,则是帝王有圣德,天下太平的象征;石马多被置于陵墓前,因为皇帝生前仪仗中必有仗马。石人6对,文臣、武臣、勋臣各四人,分别象征帝王朝会中的各级官员、将军和有功之臣。古代帝陵雕刻历来受人推崇,这些石像生造型生动,雕工精细,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。
清季以降,民生凋敝,大宫门两侧原有的护陵围墙渐次被毁,十三陵不再是皇家禁地,昔日的“官道”早已失却了皇家的威仪与肃穆。整个神道孤零零地静默于一片萧索的旷野中,四野荒芜,衰草连天。寒鸦在枯枝上聒噪,北风卷起黄沙,呼啸着穿过空荡荡的牌坊门洞,发出呜咽般的哨音。石像生们披着厚厚的尘土,有的倾倒,有的残破,在荒烟蔓草间,如同被遗忘的守陵老卒,满面风霜,神情呆滞地望着同样荒芜的远方。脚下的神道石板,多半已被泥土和杂草湮没,偶露峥嵘,也是坑洼遍布,缝隙里顽强钻出的野草,更添几分破败与凄凉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苍凉,空旷得令人心慌,仿佛时间本身都在这条通往陵寝的路上凝固、风化。而今天,石像生经过修缮,重新焕发出往日的光彩,石像的眼睛似乎有了生命,石像生两侧栽上了垂柳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柳丝拂过石像生的肩头,仿佛在为它们披上绿色的衣衫。它们依然静默,却不再蒙尘。岁月的痕迹仍在,石面被风雨打磨得光滑,甚至有些模糊,但那份威仪似乎被这新柳盎然的绿意唤醒,不再显得那么落寞孤寂。昔日帝王专享的冥途,今日成了寻常百姓漫步的幽径。
历史在这里呈现出奇妙的叠影:一面是民国乱世中荒草萋萋、石兽倾颓的孤寂长廊,一面是当下绿柳成荫、游人不绝的幽静步道。同样的石基,同样的石刻,承载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时空记忆与人间气象。
继续沿着神道前行,便能看到棂星门,又称龙凤门。这是此段神道的结束。它由四根石柱构成三个门洞,门柱类似华表,柱上有云板、异兽。在三个门额枋上的中央部分,还分别饰有一颗石雕火珠,因而该门又称 “火焰牌坊”。整体上堪称乐章第一小节华丽而精致的尾声。
再北行1.4公里左右即到达长陵神道桥遗址,民间俗称七孔桥,是明十三陵最大的桥梁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初建,桥长112.7米,每孔跨径10米,桥面宽8米。此桥既有实用的功能,又有装饰神路的功能。然而天启年间大雨磅礴,洪水不断暴涨,水势凶猛,七孔桥全部被淤泥掩埋,后又多次遇到洪水,将桥全部冲毁。如今七孔桥只剩残破的石拱券基础和公交站牌上的地名。桥下东沙河的流水与北面的天寿山、南边东西的龙虎二山完美地组成了一个水抱山环的万年吉地,放在历代帝陵中都是风水绝佳处。神道从石牌坊到七孔桥,全长7.3公里,弯曲着由西南向东北延展着伸向天寿山深处。神道两侧的绿柳成荫,与民国时期神道两侧的苍凉空旷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我在七孔桥的水边停步,俯瞰桥下水纹。旧影中的枯草与眼下的绿影在水面重叠,像两卷胶片同时显影。神道不再是裂缝,而是一条缝合时间的绿线——把荒凉与繁盛、遗忘与纪念、倒伏与站立,一并缝进七公里的柳荫。民国神道的荒芜实景,实为清末护陵制度崩坏记录。那苍凉空旷的旧影,其实并未完全消散,它沉淀在每一块石头的纹理里,隐匿在每一阵掠过柳梢的风中,与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意,共同构成了神道完整而深邃的灵魂——一条连接着死亡与永恒、荒芜与繁盛、过去与现在的路。
我忽悟:苍凉不曾消失,只是被柳荫轻轻覆了一层;空旷也未走远,只是被千万游人的笑语填得柔软。神道依旧是神道,只不过它学会了在两种呼吸里存活:一种是风穿过石缝的呜咽,一种是柳条拂过水面的轻笑。
来源:北京号
作者:史宁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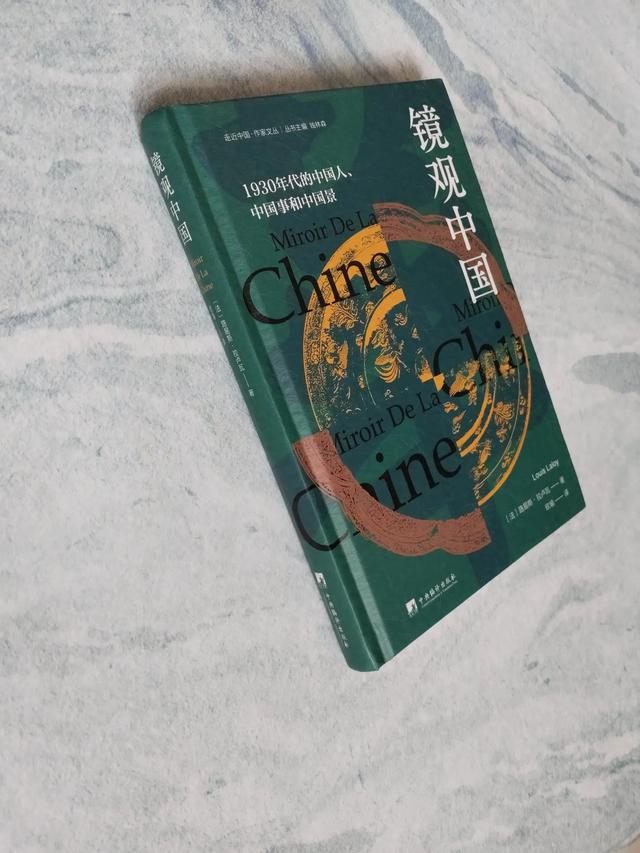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